
在1980年代末的某一天,布魯斯·門格(Bruce Menge)在一家雜貨店的貨架間漫步,思考著他遇到的一個關於浮游生物的問題。門格是俄勒岡州立大學的海洋生物學教授,專攻所謂的“元生態系統”,即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系統交匯之處。就他而言,這個交會之處正是陸地與海洋的交界處。門格的難題在於,數以億計的微小貽貝和藤壺幼蟲——統稱為浮游生物——從深海被帶到近岸,最終必須附著在某種物體上,他才能收集並研究它們。但究竟是什麼物體呢?
藤壺和貽貝能夠過濾水質並塑造海岸線,它們的數量可以反映整個海岸線的健康狀況。門格發現,計算這些變化的最佳方法是每年對它們族群進行幾次採樣,最好是在幼蟲開始定居的時候。
採集藤壺樣本相當容易:他和他的實驗室發現,船甲板上使用的防滑塗層效果很好。然而,採集貽貝樣本卻棘手得多。它們的幼蟲會附著在綠藻叢生的絲狀物和成年貽貝的足絲上——這些表面差異很大,難以模仿。他需要一種能夠像這些天然「著陸帶」一樣發揮作用,但又明顯不自然的、過於統一的材料。
就在這時,他在清潔用品區看到了它:一個紅橙色的塑膠纖維球,原本是用來擦洗鍋碗瓢盆的,但或許正是解決他浮游生物問題的完美方案。靈光一閃!就是它——Tuffy!
「我當時想,哇,這或許可行,」門格回憶道。他買了好幾個,帶回實驗室,裝上膨脹螺栓和墊圈,然後把它們固定在俄勒岡海岸幾個研究地點的岩石上,離他用來防止藤壺附著的防滑甲板不遠。門格每隔幾週就去檢查一次,三個月後,果然,小貽貝開始附著在塔菲纖維上。
幾年之內,門格和他的實驗室就開始大量訂購Tuffy海綿,數量從幾十個增加到幾百個。消息迅速傳開。這種海綿很快就成為全球海洋生物學家培育貽貝幼體的媒介。它在康乃狄克州和智利、南非和紐西蘭,以及美國和澳洲沿海地區都對貽貝有效。最重要的是,它價格實惠、易於取得且標準化。
幾十年過去了,一切風平浪靜。但有一個潛在的問題:Tuffy並非為海洋科學家設計,而是一款廚房用具清潔工具——這是一個競爭異常激烈的消費品市場。 2010年代初,儘管Tuffy在浮游生物研究領域擁有眾多擁躉,但它還是被悄無聲息地停產了。
原因乏味至極,完全是企業官方的說法。 「雖然很多消費者喜歡這款產品,但市場需求不足以支撐我們繼續銷售SOS Tuffy。」Tuffy由SOS公司(全名為「拯救我們的平底鍋」)生產,該公司於1994年被高樂氏公司收購。高樂氏公司悄悄地停產了Tuffy,同時推出了另一款名為SOS無刮痕清潔刷的產品。雖然這款新產品有時會被誤認為是Tuffy,但海洋科學家、鑄鐵鍋收藏家以及亞馬遜上的評論者都一致認為它不如原版。 Tuffy即將停產的消息一經傳開,研究人員便開始四處搜尋,在eBay上以遠高於超市價格的價格大量購買,並在市場上尋找可能的替代品。
在研究海岸線生態系的海洋科學家圈裡,Tuffy海綿的停產猶如一場海嘯。但對高樂氏公司而言,這不過是消費者需求海洋中微不足道的漣漪。有人認為這種海綿在它原本的設計用途上還有進步的空間。門格也這麼認為。 「Tuffy海綿的問題在於,」他說,「它其實並不怎麼好用。但它們對吸引貽貝非常有效。」這種纖維球已經成為標準產品,正因為如此,貽貝研究才依賴它們。
有一種經濟和組織理論可以幫助解釋Tuffy搶購事件:它被稱為路徑依賴,這個名稱幾乎完美地描述了它的本質。一旦某種路徑形成,某種標準確立,就很難放棄。路徑依賴的信徒(包括從企業高管到進化經濟學家等各行各業的人)喜歡說「歷史很重要」 ——這意味著從鐵路軌距的特定寬度到VHS在20世紀80年代錄影帶大戰後最終勝過Betamax,一切都取決於過去的某些特殊情況。
布魯斯·門格在一家雜貨店的過道裡偶然發現了一個鍋刷,不久之後,海岸線生態系統健康研究就依賴於「塔菲號」了。但突然間,一件罕見的、甚至是歷史性的事件發生了:「塔菲號」消失了,研究方向也隨之分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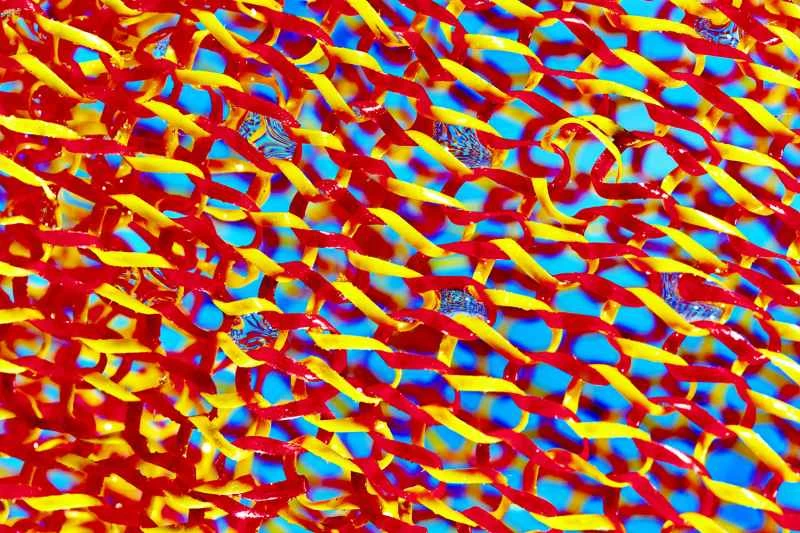
科學家經常會重新利用市面上常見的商品:用茶漏篩骨頭,用牙刷擦洗樣本,用瑜珈墊做魚類手術台,用指甲油追蹤並根除蠅蛆。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海洋科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物學家珍妮佛‧卡塞爾(Jennifer Caselle)在這方面頗有心得。幾年前,她在一次關於這個主題的演講中指出,維多利亞的秘密的琥珀浪漫香水在野外生物學家中被公認為最好的驅蟲劑之一。施樂公司生產的防漏紙在水下數據記錄方面表現出色。但當製造商更改配方,使其不再適用於水下環境時,「海洋科學研究一度幾乎停滯了一兩年。」她是在開玩笑,但隨後語氣嚴肅地補充道:「施樂公司都不知道。這就是為什麼重複利用很危險,因為你可能會失去它,而他們」(指產品背後的公司)「根本不會。
雖然消費者失去他們已經使用並習慣的東西會感到難過——甚至有專門的論壇討論停產的Tuffy——但他們對這些產品的依賴程度與研究人員截然不同。洗碗工具和科學標準之間存在著本質區別;對於後者而言,即使是最接近的替代品也可能引入變量,從而導致數據偏差。
一些經典的路徑依賴例子風險要低得多。即使面對其他更好、更有效率的佈局,QWERTY鍵盤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但很久以前,我們選擇了QWERTY作為標準,所以我們只能繼續使用它。至於我們是如何被這種佈局束縛的,至今仍存在爭議;一些歷史學家指出,在19世紀80年代末的一次全國打字速度比賽中,獲勝者秘密記住了QWERTY鍵盤的按鍵位置,因為——據說——這種佈局完全沒有道理。
對於研究海岸線生態系統的海洋科學家來說,Tuffy 停產猶如一場海嘯。
現代生活的許多面向都是如此:偶然的碰撞讓我們走上了看似不合邏輯卻又堅持了很久的道路。想想汽車——那種需要我們從地裡挖出化石浮游生物並點燃才能驅動的汽車。在早期,蒸汽汽車和電動車與內燃機汽車一樣受歡迎,甚至更受歡迎。但勘探者不斷發現大量的石油;石油運輸成本低廉,而且能夠快速且方便地提供龐大的能量。最終,石油勝出。意識到我們開闢的道路、我們設定的標準並非源自於殘酷的邏輯,而是歷史的偶然巧合,可能會讓你感到沮喪,甚至詛咒命運。或者,如果你是科學家,這或許會激勵你捲起袖子,著手尋找前進的方向。
卡塞爾和她的實驗室透過重複利用舊的Tuffy海綿來應對這種情況,但這遠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首先,研究生要將每塊海綿展開,使其從球狀狀態解體成細長的圓柱形,就像漁網襪一樣。然後,他們小心翼翼地將「襪子」鋪開,擦掉上面的碎屑,包括貽貝和蛤蜊的幼蟲以及其他各種小型海洋生物,並將所有碎屑收集到一個分揀盤中,以便之後在顯微鏡下進行檢查。生物學家隨後沖洗Tuffy海綿,並將它們鋪在一個巨大的紙箱邊緣。在這個紙箱旁邊,還有一個相同的紙箱,裡面裝著重新組裝好的、可以立即使用的Tuffy海綿,它們被重新捲成球狀,並用紮帶兩兩捆紮在一起。這些重組的纖維球最終將被綁在繫泊繩上,然後被拋入太平洋,距離海岸數百碼遠。
在分類站下方放著一個裝滿木製甲板刷的箱子,這些刷子用於收集海膽幼蟲。在科考船上,卡塞爾還使用SMURF(標準化魚類補充監測單元),這些裝置由花園圍欄和雪柵欄製成,模擬海藻冠層,許多幼魚和一些小螃蟹都在那裡安家。和大多數實驗室一樣,卡塞爾的實驗室也使用任何人都能買到的物品,並將它們重新用於科學研究,希望公司不會將它們從市場上撤下。
當卡塞爾第一次聽到「塔菲大消失」時,她當然很擔心,但也沒那麼焦慮。沒錯,她四處打電話詢問是否有替代品。但她的實驗室其實已經有解決方法了。她一直很不願意丟掉這些清潔刷(「瞧瞧我們,海洋科學家,為了研究竟然要丟掉這麼多塑膠!」),所以她制定了一套拆線、晾乾、再重新捆紮的流程。
不過,她知道這些存貨不可能永遠用完,現在網路上也很難再找到。 (即使是Clorox公司出售的替代品,在eBay上也只能賣到35美元一對,而且賣家都是專門用來洗鍋的。)她想過試試其他海綿,看看能不能用,但後來意識到,如果換用其他海綿,可能會影響數據集的完整性,於是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3M公司曾經寄來一箱Dobie牌的海綿,說要用在另一個實驗。結果發現,這些海綿在各方面都比不上Tuffy牌。織得太密,不夠柔軟,總之就是不行。 「我的天哪,你們想要嗎?我們討厭它們。」她說。
如今,不再像以前那樣「笨手笨腳」的門格(卡塞爾稱他為「塔菲爺爺」)最近重新關注起他的歷史數據,試圖從中探尋海岸浮游生物種群可能隱藏的海洋和氣候秘密。具體來說,他一直在研究海洋熱浪期間和之後貽貝和藤壺的補充量是如何變化的。海洋溫度的這種飆升會引發極端天氣事件和物種死亡,以及其他不良影響。他說,這些熱浪「肯定會成為未來的常態,更加頻繁、更加強烈,並對沿海生態系統構成真正的重大威脅」。 2021年6月,一場破紀錄的酷暑襲擊了太平洋西北地區,沿海溫度超過華氏120度(約攝氏49度),估計導致沿海生物死亡達10億隻。一些地區的貽貝床幾乎完全崩潰,這幾乎可以肯定預示著整個生態系統的更大範圍崩潰。
貽貝似乎在預示著即將發生的事情。 2020年發表在《PLOS One》期刊上的一項回顧性研究,分析了2011年和2012年的數據,探討了貽貝的鈣質外殼如何反映出海洋酸化加劇的趨勢——這是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的結果。另一項研究則著眼於貽貝族群模式如何揭示潮汐變化和新的上升流模式。這些研究都利用塔菲浮游生物作為幼蟲的招募工具,將浮游生物本身作為生態系統的風向標:它們固著於特定位置,壽命較長,並收集來自洋流的物質。
如果貽貝能夠感知任何事物,它或許會了解自身的歷史,畢竟它就生活在歷史之上:新生的貽貝常常附著在舊貽貝之上,形成一種軟體動物的“羊皮紙”,有些貽貝甚至可以活到50歲。但即便雙殼類動物知曉這些變化,它們又能如何應對這變幻莫測的水域呢?它們又該何去何從?貽貝一旦紮根,其遷徙路線便無法改變。而我們人類的遷徙路線卻可以改變。但這需要我們付出努力,需要我們用心關注這個日益岌岌可危的世界所發出的種種跡象和訊號。有時,這些訊號就來自意想不到且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塔菲貽貝」事件的教訓並非在於美國企業的反覆無常就能推翻數十年的科學成果——畢竟,研究人員已經適應了新的現實,並繼續研究,重新審視舊數據,重複利用舊的「塔菲貽貝」。真正的教訓在於貽貝本身,以及它們能教導我們的一切,它們一直以來都在警示我們。門格回憶說,多年來,他的同行一直認為貽貝族群變化的數據無關緊要,只是事後才想起來的。 「我們沒有思考過這種(貽貝種群的)變化發生的原因,以及背後的因素,」他說。當時普遍的看法是“這可能並不重要。但事實證明,它非常重要。”
閱讀更多《大眾科學》文章。
